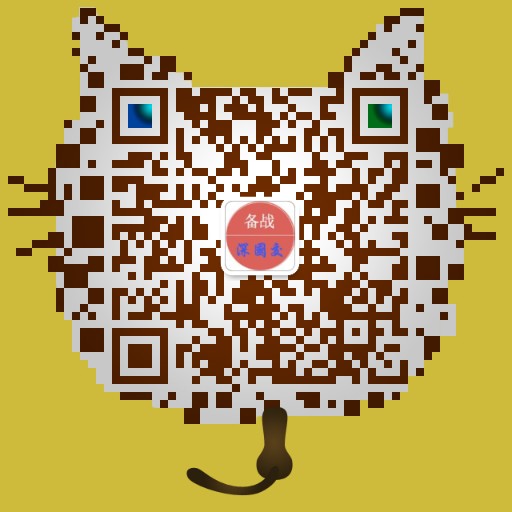当前位置:首页 » 深国交哲学社 » 正文
-

安东尼奥·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作者 / 彼得·托马斯 排版 / 亦源 在20世纪90年代反对「新世界秩序」的抗议浪潮,特别是新千禧年代在政治哲学中被记录下来的各种政治和社会运动中,一些形式再次对「政治域」 (the political) 的本质及其与「政治」 (politics) 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关注。即便在它们表现出踌躇、软弱,又遭到了挫败的情况下,也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运动仍然引发了关于这样一个议题的争议,那就是如何开展协作——这对在今天界定一种现实主义的左翼政治规划是必不可缺的。这些讨论进一步又重新开启了哲学实践能够为政治解放规划做出怎样的贡献的问题,这种倾向至少已经在具有重大意义的「少数派」 (minoritarian) 潮流中初露端倪。 
「政治域」的回归
以图式的方式来看,在当代左翼政治哲学中关于「政治域」之本质的问题上,我们可以区分出至少两个宽泛的「阵营」或进路。一种潮流——这种潮流由于与主流哲学中规范性问题的复兴产生交叉而得到了加强——试图将「政治」和一种特定的、具有奠定意义的「政治域」概念之间的关系加以形式化,后者为前者提供了根据或来源。于是,规定政治域之本质被视为阐明政治实践的必要条件,这正是因为,政治不过是被再现为「政治域」结构在形势中的例示化罢了,而「政治域」的结构则总是超出了政治,且必然地超出了政治。左翼政治哲学家(特别是英语世界)对于卡尔·施米特这一形象的重新发现或许已经成为了这种方案的标志,尽管其意义绝非仅限于此。[2]对于那些没有很好地伪装起来的「柏拉图化」理论,如施米特以及由他衍生出来的诸种现代翻版来说,「政治域」没有通过政治而被生产和构成出来,甚至还被政治压抑了;相反,「政治域」对于政治来说是生产性和构成性的,它在时间和逻辑意义上都先于后者。在这种视角看来,「政治域」意指着人类经验的一个自主且不可还原的领域,其基本的结构和逻辑截然不同于其他同等自主且不可还原的领域:「社会域」、「美学域」等等。因此,正如任何具体的社会实践都分有了社会域的「逻辑」一样,任何具体的政治行动都必须分有「政治域」的逻辑,并且在这种逻辑中寻获其意义。[3]
无论施米特的政治域概念有时就其激进而逼真的现实主义发表了什么样的主张,它在现实中都分有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一个最为悠久的幻想:那就是,它独断地断言了一个规定诸偶然事件并为它们提供了本质的环节。作为思考政治域的特定哲学形式(和只能分析「单纯的」政治的现代政治科学不同),政治哲学声称自己对通达这一环节具有特权,它是一门症候性地解读政治域之踪迹的艺术,而政治域的本质恰恰就是永远在政治世俗或具体政治活动中保持遮蔽的本质。然而,这种主张当然是重言式的:就政治域的概念本身已然是一个形而上学建构而言,某种形而上学的哲学不可能不对通达它有着特权,二者是相互确认的关系。在这种完全传统的进路中没有得到思考的,是政治域的概念空间在哲学中的生产以及哲学本身的构造,政治域通过诸种物质形式实现其对于政治的领导权,而哲学断言它同时掌握了二者。
另一种潮流——或许可以被界定为当代政治思想中的重构「先验」模式——试图通过规定真正的激进政治参与之可能性的条件来破坏这种传统的政治域概念。[4]实际上,这种进路提出了一个「真实政治」或「真正的政治」的概念,来取代对于传统政治哲学和「官方」政治的苍白模仿。例如,齐泽克在与施米特,以及更一般的「全部政治思想史」——「最终不过就是对于政治对抗的逻辑本身的一系列拒认」——的论战中指出,「一种左翼的立场应当坚持的是,固有的对抗,作为政治域的构成性因素,具有无条件的优先性」:「穿越了社会机体的内在斗争」。[5]
在齐泽克看来,政治域就这样最终在社会域中找到了它的基础,或者说,它正是对于社会域的构成性内在对抗的抑制,而社会域又需要政治域作为解决其自身张力的地域而出现,于是反过来被现存政治抑制和扭曲。阿兰·巴迪欧以及其他一些与他有关的人物,如席尔万·拉撒路 (Sylvain Lazarus) ,以一种相似的方式从当代的诸种政治和社会冲突形式开始;他们认为,在今天,一种真正的激进政治只有同国家保持某种「距离」,在一个没有被巴迪欧称之为「资本主义议会主义」——这个后毛主义的表述十分古怪地令人回想起博尔迪加——的逻辑所污染的空间中,才能够存在。[6] 当代的「官方」政治不过是「真实界」的畸变,而「真实界」才是真正的政治冲突发生的场所,用巴迪欧一针见血的话来说,在那里才可能产生「一种不同性质的政治」。[7]
在这种进路中,哲学的作用在于将这些「真正政治」的时刻的产生把握为「真正的」政治域的症候,区别于那些拒认它们的形式(齐泽克)或者伪装性的冒名顶替(巴迪欧和拉撒路)。然而,值得商榷的是,在为当代政治运动给出能够为我所用的解释这方面,这种潮流是否就比前者更加可信,毕竟这些运动要么是将「政治域」的空间再一次构造为现存状况,而哲学也在这个构造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要么就是二者相互加强了政治的支配性本身,隔绝了信任决断论的诉求: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在近来英语政治哲学的辩论中并不具有显著地位。当代知识界文化对于葛兰西的引述受到了「新葛兰西主义」范式的影响,这种范式更关注的是将葛兰西呈示为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分支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一种可行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而非用于直接的哲学问题。因此,观察对于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阐释史是如何以上述两种当代进路的各种变体为标志的,就更加有趣了。例如,陶里亚蒂将《狱中札记》阐释为一种能够为意大利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策略提供支持的「一般政治理论」的梗概,举例来说,他倾向于以与强基础主义的政治域概念相一致的方式来呈示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葛兰西的天才就在于,他是能够被纳入西方政治哲学「经典」这一万神殿的最有力的马克思主义候选人。另一方面,欧洲共产主义者日后将葛兰西拥护为现代化和发展的理论家(据说,葛兰西为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诸多「历史性妥协」[historical compromises] 提供了正当理由),同时又将他的市民社会概念解读为政治权力的真正场所,它只是随后才从形式上被现存国家形式扣押起来。因此,夺取政权需要在「国家之外」进行艰苦的先期建设工作,以剥夺其支持。最近有一些人尝试将葛兰西和施米特勾连或综合起来,他们要么认为葛兰西和施米特的思想在某些关键方面是可兼容的,要么认为施米特为葛兰西思想中的缺陷提供了有益的纠正。[8]
尽管有着上述以及一些其他的阐释传统,我仍然保持这样的观点,那就是在今天,对《狱中札记》进行一种更少被过度决定的解读能够分辨出一种在柏拉图化模式和先验模式二者之外的替代方案,或者至少是识别出一条可能出路的轮廓。《狱中札记》试图借助一种领导权理论,从而以非形而上学的且具体的方式来重新思考政治域的概念。按照这种解读,葛兰西并没有给出一种关于「政治域」本身的理论,更不用说一种「一般政治理论」了。相反,他试图给出的是一种对于「生产」的分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将「政治域之构成 (constitution) 」——这种构成既是能动 (active) 意义上的,又是形式化 (formalized) 意义上的——分析为一种位于《狱中札记》中所描述的资产阶级「整体国家」 (integral state) 之中的独特的社会关系。「领导权」描述了这种构成的过程,或者可被历史性地辨认的政治实践——有关一个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 (social group) 之规划的交往、协作和组织的诸种社会关系——得以界定「政治」本身之本性的方式,这些政治实践将其界定为这个过程在政治和哲学上的「馏出物」。反过来说,这一分析也为这样一种尝试打下了基础,那就是去尝试思考「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 (of a completely different type) 政治域概念的可能性(在这里借用列宁对于1917年「两个政权的过渡时期」的苏维埃政权的地位的描述[9]),从这种「政治域」的概念和实践中便能够形成葛兰西所谓的「自我调节的社会」 (self-regulated society) 。
这一分析的核心是葛兰西《狱中札记》的总体计划中的三条研究主线,其中后两条是通过前一条的视角得到解读的:第一,关于诸种社会实践之间的可译性的一种非本质主义理论;第二,对于哲学的一种非形而上学界定;第三,对于迄今一切哲学和(资产阶级)国家形式(用葛兰西的术语来说就是「整体国家」)之间的整体关系的批判,这种国家形式被设想为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或政治域的制度化形式二者的辩证统一。本文的目的在于阐明这个三重的理论运动的部分崭新要素,并提出今天的激进政治的一种可能的意义之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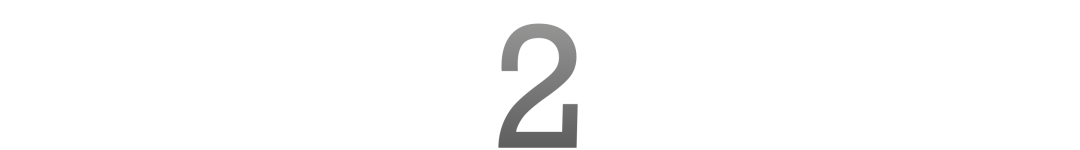
可译性,思辨 与作为「形而上学事件」的国家
列宁在1922年共产国际四大上指出,俄国革命还没有被「翻译」为西欧各国的语言,这第一次激发了葛兰西去阐述一种可译性理论。[10]作为一位语言学家,葛兰西探索了这个谜一般的陈述在各种语境下的意义,特别是比较历史语言学及其对于方言和民族语言之间关系的分析。[11]这也是他关于哲学和政治(以及历史)之间关系的理论的核心,这种关系是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关系「凝缩」而成的主要代表形式。在1931年,葛兰西详尽地批判了克罗齐为哲学设定一种「非政治的」或纯粹「哲学概念性的」基础的尝试,他表明
于是,我们就抵达了「哲学与政治」、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平等或相等,也就是抵达了一种实践的哲学。一切都是政治的,即便对于哲学或种种哲学也是如此……而唯一的「哲学」,就是行动中的历史。[12]
葛兰西并没有将哲学与政治、思想与形式之间的关系设定为等级性因果的诸种还原或派生的形式,也没有设定为其本己的逻辑所支配的诸种区别而自主的领域之间的外在勾连甚或过度决定,而是设定为一种既同一又区别的辩证关系。这种同一性并没有被设定为一个基础性本质的功能,一个被「表达」并且从而被「实现」于不同的地域形式的本原性统一。相反,哲学与政治的同一被设想为不同组织层级之间的一种持续转译的能动性关系,它形成了一个阶级的或社会集团的活动;正是这个转译到不同的语域的活动回溯性地而又暂时地「统一」了一个阶级的规划,从而使其哲学和政治维度得以被把握为——用斯宾诺莎的概念结构来说——一个既已实现的而非本原的「实体性」的「属性」。换言之,对于葛兰西来说,不存在原语言 (Ursprache) ,正如不存在一种在同质化的世界语中达成直接可理解性的目的一样;对葛兰西而言,「可译性」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实践之间的沟通关系在本性上始终是未完成的,因而也是可转化的。[13]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870年4月22日—1924年1月21日)
进一步说,这些形式之间的区别被把握为「量性的」,而不是「质性的」,这种区别与社会关系的组织、确证与争辩的不同强度有关,而不是先于这些形式的诸种互不兼容的逻辑之间的不可逾越的区别。在这个视角下,哲学是社会的知识关系之组织的一种极强的形式,政治实践便在这种关系中发生,因此,哲学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被高度中介了的制度性的和话语性的政治实践形式了。同样,就政治试图调整社会关系的组织,而知识又组成了这些社会关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言,政治本身也已经是一种经过高度中介的哲学实践形式了。也就是说,政治被理解为「处在实践状态下的」哲学。
这种非本质主义的可译性概念为葛兰西的如下主张奠定了基础,即形而上学代表的并不是哲学的「坚硬内核」,而是哲学的诸种可能的形势「形式」之一。尽管可能和我们今天这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所区别,和他那一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的是,葛兰西仍然拥护十九世纪晚期广泛的形而上学批判中一个特定的版本,这种版本由马克思阐述并由晚年的恩格斯所「通俗化」。这一批判坚持认为,形而上学概念必须合理地转译为它们真实的历史实存形式,转译为社会上特定的以及时间上有限的话语形式,仅仅错误地主张具有普遍的和非历史的有效性。在葛兰西这里,后马克思主义者克罗齐对于这一批判的歪曲以及将其应用于马克思的思想本身的尝试促成了一个意义深远的扩展和澄清。葛兰西按照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将「思辨」指认为形而上学这种哲学形式的核心或「生产方式」。[14]
正如葛兰西指出的那样,克罗齐声称自己「谋求从哲学领域中『驱除』一切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残余,直到否定掉一切哲学『体系』为止」。[15]与此同时,他断言,马克思主义及其伪概念代表的不外乎是形而上学传统中的二元世界解释的一种变体。晚年的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结构」「归根到底」决定了其他的社会实践,对于克罗齐来说,这不过是柏拉图的理念的现代变体罢了。克罗齐阐述了后来几度被后马克思主义的浪潮——往往在无意中——加以利用的一套哲学坐标,他提出了这样一种批判,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本质主义的」:它只赋予结构以完全的现实性,而将上层建筑仅仅当作纯然的显象、模仿的失败或者现象来把握。克罗齐声称,马克思主义对真实的历史依旧漠不关心,因为它已经宣称真实的历史在本质上就是不真实的了。
葛兰西出于切身的利益而回应了这一指控:如果克罗齐在唯物主义史观的初始命题中仅仅看到了一种思辨形而上学,那是因为他本人的思想在本质上就是思辨的。[16]马克思的结构概念中的历史动力就是能动的社会关系构成的整体,而克罗齐未能把握到这一点,因为克罗齐的体系在历史实践以及用于理解这些事件的概念性之间设定了不可逾越的区别:换言之,这正是因为克罗齐在他错认的否定时刻中无意间重建了形而上学。对于克罗齐来说,以哲学概念的形式出现的真正思想的结构必然是不为历史发展所玷污的(和实践行动中运作的单纯的「伪概念」不同,这些「伪概念」被斥之为工具性的「意识形态」)。[17]哲学概念在作为思想的思想中被给定为一个「更高的」、思辨的、关于真实界的知识形式,涤除了实践的纷扰。[18]思想至多可以在窥镜的意义上反映历史(或多或少是如此,这取决于概念的「纯度」),但它不能参与到其中,它的基本「逻辑」结构也不会被历史所变易。葛兰西认为,克罗齐本人将历史和哲学同一起来的尝试,就这样被困在历史的「观念」当中,而不能理解它自身的历史性。它只能假设着去反映现实,好像在现实外面一样,而不是作为现实的一个要素,来体认自身的实践构成——换句话说,这种「哲学」本身以及它的纯化概念的地位就是「意识形态」的实例,或者对于当下的概念与政治组织的实践性介入。

贝奈戴托·克罗齐,意大利著名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哲学家。 因此,对于葛兰西来说,问题就在于将这种思辨倾向破译为阶级规划之政治发展的一个指标,或者将思辨解析为「它的真实项即意识形态」。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形式并不是定义了哲学本身,相反,它被认为是意识形态构型之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它是一个既已实现的社会与政治领导权之阶段的症状,这种领导权凭借理念的提炼和概念的完善来确保自己不会解体和崩溃。[19] 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哲学被界定为实践性的社会关系中之一种而言,思考哲学试图理解的社会关系为哲学带来的改变,或者换句话说,将思想本身的地位思考作交往、协作和组织的社会关系,就是可能的。
可译性概念在葛兰西对黑格尔国家概念的批判性改造中同样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与青年马克思的批判是一致的。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法哲学中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失败的过渡不仅透露了黑格尔政治哲学中的缺陷,或者黑格尔的辩证法和一般哲学中的缺陷,而且透露了现代国家本身的基本现实。马克思表明,「黑格尔应该受到责难的地方,不在于他按现代国家本质现存的样子描述了它,而在于他用现存的东西冒充国家本质。」[20]对马克思来说,黑格尔的思辨实体化给出了现实的一幅过于真实的肖像,是最完全意义上的模仿失败:黑格尔的范畴仅仅是模仿——或者用葛兰西的话说,仅仅是「转译」——并且追认了一个外表,这个外表并不单单是本质的表达,而且是由对于一系列复杂的政治中介的压抑造成的。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现代的资产阶级国家本身就是一个突出的「形而上学事件」。用葛兰西的话说,它是思辨具体地实现为了一种广泛的社会组织形式。
葛兰西用「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辩证统一的概念,批判地扩展了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批判。「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这两个实例分析地来看是可分的,但在资产阶级「整体国家」中却「有机地」统一在一起。[21]对于葛兰西来说,资产阶级整体国家的「政治社会」(这个术语在葛兰西的意义上不仅意味着「官方的」政治,而且还意味着贯穿于社会构型当中的组织和协调作用)是市民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力量和组织形式的一种特殊的「凝缩」(用波朗查斯的术语来说),而又是政治社会本身使得市民社会成为可能,或者至少对其加以过度决定。[22]政治社会就是对这些社会关系的制度性组织,或者用思辨的术语来说,是对它们的理解 (comprehension) 。和马克思一样,葛兰西反对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真正基础,而不是相反。然而与此同时,同样和马克思一样的是,葛兰西也承认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国家(在这里被理解为在「政治社会」的关系中得到体现的具体制度作用)确实是首要的,因为它是统属并组织了市民社会的真实抽象或实体化。市民社会被这个现存的政治社会所「包裹」并相互渗透,只能作为后者属下的「原材料」。[23]也就是说,政治社会将自己设定为对于市民社会的一种思辨性理解,正因为政治社会宣称自己是实施组织的普遍性的一个实例,市民社会才会在具体性中被构成出来。用施米特的术语来说,这是「政治域」支配和组织「政治」这一要求的制度性实现;用葛兰西的术语来说,这是对资产阶级规划的思辨转译。
这一凝缩或思辨转译在历史上是由资产阶级通过一种全新的政治实践而实现的,这种政治实践便体现为《狱中札记》中出现的一种「领导权」概念。[24]葛兰西在《狱中札记》全书中对政治域在不同国家背景下的构成过程进行了大量研究。资产阶级领导权是一种独特的现代政治实践,它试图将原子化的、法律上自由的个体组合成为更大的集体性社会团体,贯穿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之间的边界;作为一种组织以及领导的形式,它既是「公民的」的同时又是「政治的」。资产阶级的规划正是通过协作和管理的社会关系而实现了从单纯的(经济)法人到名副其实的领导权阶段或政治阶段的过渡,成功地将自己的特殊利益——首先是私有财产这一形式——设定为对于社会整体都是有效的。迄今为止,政治社会的历史都是由它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有意识的分离所构成的,是对于法人市民社会中的诸种社会力量之间的矛盾的思辨的、法律的解决。也就是说,资产阶级领导权的实践本身,就是使得「政治域」被「构成」为社会经验中的一个独立领域,被具体地生产和制度性地定型为一切可能的「政治」之基础的途径。事实上,就独立的政治社会是一种只有在现代社会才会出现的社会形式而言,它也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界定为资产阶级政治社会,这与黑格尔那里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相似——正如政治域可以恰如其分地从这个视角出发被界定为「资产阶级政治域」一样。
这种视角本身就足以批判那些柏拉图化的或者规范性的「政治域」概念,这些概念将「政治域」设定为一个先于政治的环节并且对其加以规定的空间。这种传统的西方政治哲学潮流断定,在政治域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类性与个性、概念性与例示化、规定与有规定性的关系;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则反对这种潮流,它试图证明,资产阶级整体国家的政治域并不是构成性的 (constitutive) ,相反,它是在明确的制度条件下历史性地被构成的 (constituted) ——这些制度性的条件包括,并且或许首先就在于「政治哲学」之认可的制度性形式。按照葛兰西的分析,「政治域」代表的既不是一种起源,也不是从「政治」中的偏离,而是政治以及哲学上的组织的一种经过高度中介的形式,是资产阶级的领导权规划在哲学上的「馏出物」。它是与在政治社会中既已存在的思辨结构相对应,并对其加以组织的思辨概念性的层次。一种提出「政治域」这一概念的政治哲学仅仅重复了将特定的政治实践单边地、永久化地转译为思辨的形而上学概念的过程,而这种概念却早已被资产阶级领导权所实现了。
不过,葛兰西的整体国家概念也同样为我所说的当代政治思想中的「先验」模式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视角,对于其他有着相似的实践后果的进路也是如此。现存的政治社会及其在资产阶级政治域中的组织逻辑并不仅仅是一些应当消失的幻觉,或者应当避免的位置。相反,它们是实体化或者真实抽象,其存在样式恰恰在于它们同政治之间积极地建立起来的思辨性关系,无论政治「距离」国家有多远:资产阶级政治社会以及伴随着它发生的「政治域」将「真实政治」设定为它们的对象,以便以各自的方式「沉思」这个对象,政治域试图对发生任何具体政治行为的可能性加以规制和支配,正如政治社会在法律上对这些行为的具体实现加以管制一样。因此,问题并不在于一个从现存的政治社会中减去形变的部分,来揭示「政治」在真实界中的坚硬内核,无论这个内核是社会对抗、市民社会,还是一个超越了市民社会的无规定场所。相反,就资产阶级政治域的实体化形式在实际上规定了一个概念空间,而社会构型中的政治——不仅仅是「官方的」政治,而且也是更广泛的、葛兰西意义上的政治,也就是社会关系的组织——只有在这个概念空间中才能够发生而言,政治域的作用更多地是规定了实践的具体形式,即使这些实践的条件属下于现存的政治社会或者被其所询唤,能够从其内部破裂其物质构成,而且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事情也是如此。也就是说,这些形式的活动和组织可能足以形成「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政治域构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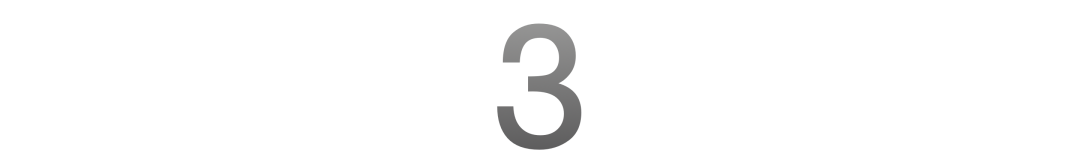
走向作为「哲学事实」的领导权
正是在非资产阶级领导权,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理论中,葛兰西尝试勾勒出一类这样的政治实践,这些政治实践能够构成新的「政治域」概念以及「政治域」实在。葛兰西并没有将这样一种「政治域」概念设置为一个基础性的、区别于且先于「政治」的规制性审级,而是将其设置为一个位于「政治」内部、与「政治」同时发生的理论环节。对列宁的引用再一次对葛兰西的理论阐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1931年,葛兰西提出,晚期列宁在后革命形势下「对领导权的理论化与实现」——葛兰西的重点同时放在了这两个术语上,亦即既是理论化又是实现——「构成了一个伟大的『形而上学』事件」。[25] 葛兰西在这里指的是列宁的这一尝试:在第一个广泛的工人「非国家国家」 (non-state state) 中制订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使得俄国无产者(特别是工业无产阶级)能够与其他被压迫阶级(首先是农民)建立「复合体」 (composite body) ,为他们在广泛的政治形式中提供民主领导与民主参与——尽管这种尝试受到许多限制,并且最终遭遇了悲剧性的失败。[26]这是一个「『形而上学』事件」,因为它破坏了既已构成的国家形式、其政治社会与政治域逻辑的稳定性,而这些被理解作诸种「被制度性地实现的」形而上学形式。这一尝试意在通过积极地展示一种替代性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使其基于彻底不同的、非思辨性的和非等级性的原则——至少是展示出它的可能性——从而将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从资产阶级政治域的概念性中剔除出去。
然而,在1932年,葛兰西试图更进一步,将这一洞见推广为一种特定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实践理论,使之能够被转译为其他欧洲国家的「语言」,这些国家分别有着不同的传统和不同的阶级构成。所以,葛兰西成熟的领导权理论包含三个从整体上相关的「环节」:首先,尝试将俄国革命之前列宁对于后革命形势下的领导权概念的实践发挥「转译」为理论术语;其次,将这一理论用于研究资产阶级政治域在西方的历史性构成(这被视为对于东方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实践的回溯性否定的形象);第三,进一步将这一理论转译为建立起一种组织形式的具体倡议,在这种组织形式中,西方的大众阶层在位于「经济活动的决定性核心」(也就是能够在生产领域否定资产阶级的物质支撑的工薪阶层)的部门的领导下,可以被统一为一股能够与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相对峙并将其击败的政治力量。[27]

1932年是葛兰西的奇迹之年,在这一年里,他阐述了狱中的批判研究的几个部分,并将它们制订为一个「实践哲学」的积极计划,将其作为大众阶层的这种政治组织形式和领导形式的必要组成部分。在这里只能说明这个运动的最一般梗概,也就是它对于替代性的政治域概念的描述。实践哲学计划的核心是阐明一种不同的哲学「形式」,它不是思辨的或形而上学的,这些形式——遵循着青年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批判——与资产阶级国家这一「形而上学事件」形成了合谋关系,相反,这种哲学「形式」是一种能动的社会知识关系,它试图加强大众阶层政治介入的「凝聚力」。这种哲学——用拉布里奥拉十分贴切的话来说,「内在于它所哲学化的事物」[28]——并不是对于在它之外者从观念上加以统一和支配,而是对于社会关系之整体的自我组织的「转译」,或者说是内在于这一自我组织之中的理论环节。
葛兰西认为,这种实践哲学必须生产出理论与实践之间能动且持续的「同一化」[29] (identification) ,而非单纯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或者对于诸离散要素的外在勾连。他表明:
如果我们提出了如何生产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同一性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在这个意义上被提出来的:在一个确定的实践的基础上建构一种理论,使其与这个实践中的决定性因素相一致和同一起来,如此一来就可以加速正在发生的历史过程,使得实践在其全部因素中都更加同质、凝聚和有效,最大限度地加强它;或者,在一定的理论立场上组织起不可或缺的实践要素,从而使理论发挥效用。理论和实践的同一是一个批判的行动,通过这个行动,实践才被证明是理性的和必然的,理论才被证明是现实的和理性的。[30]
就这样,对理论与实践之同一性的生产成为了这样一种批判性的艺术,它以一种斯宾诺莎主义的方式,一方面为实践寻找一种合适的理论形式,这样就能够增强行动的能力,另一方面又为理论寻找一种合适的实践形式,这样就能够增强认识的能力。[31]这种非形而上学的哲学形式并不是作为国家形式实施支配的一个功能,而是被重新定义为一种赋能的教育学 (enabling pedagogy) 的关系。它试图作为对于现实存在的实践的理论理解来展开行动,将潜在发展的倾向与路线描述为具体的组织和协调行为,而不是规范性地、自上而下地规定它们的必然形式。
如果把这种哲学形式转译为政治术语,它就是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规划本身的一个能动维度,这一规划被设想为潜在广泛的、非官僚的组织形式,它表明了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政治域构成的可能性。传统的关系被倒置了;社会关系之组织(也就是政治)的物质性断定了自己对于思辨概念性中对其的理解(也就是「政治域」)的霸权。这时,一种不同类型的政治域的轮廓便浮现出来了,这种政治域与政治是结合起来的,而不是分离开来的,它被配置为实践之自我理解的理论形式,与实践在持续的转译关系中整体性地关联起来。
因此,到了1932年5月末,葛兰西回过头来考虑列宁晚年在理论上,并且尤其是在实践上发展一种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形式的尝试,并在一个非形而上学的语域中阐述了这一尝试的重要性。他指出,
就他推进了政治学说和政治实践而言,伊里奇也推进了作为哲学的哲学。就实现一种领导权装置 (hegemonic apparatus) 创造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地形而言,这一实现也决定了一种对于意识的和对于认识方法的改革:它是一个关于认识的事实,一个哲学事实。[32]
于是,葛兰西从作为「形而上学实践」的资产阶级国家理论——这一理论被资产阶级领导权的政治域构成生产出来,在一个独立的政治社会中得到制度化,并被其官方政治哲学所强化——进展到了一种作为一个(潜在的)「哲学事实」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实践的理论,它旨在将哲学和政治、思想和行动在一个自我调节的社会形式中统一起来。

「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政治域」
作为一种对于(资产阶级)政治域的构成的分析,以及一种基于实践哲学而提出的、对于替代性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形式的概述,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在今天有着怎样的现实性?在葛兰西的时代,葛兰西遵循着列宁,强调要强化少数的工人阶级与多数的农民之间的政治关系;而自这一时期以来,在大多数的国家构型中,政治地形都已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虽然在现在,这种「辩证教育学」的关系在国际的地形上被建立了起来,构成了当代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最新阶段的斗争的最为重要的前线之一。商品形式持续地渗透到生活的一切领域当中,劳动过程被以「后福特主义的」、「高科技的」或不稳定的新自由主义形式重新组织起来,以及随之而来的传统的工人阶级身份和社区的解体,这些现状似乎都在否认这种理论仍然存在物质支撑,尽管雇佣劳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为广泛。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的重大政治失败以及左翼组织形式的不断崩溃,与葛兰西所描述的作为「斗争组织」的「现代王子」构型都相差甚远。[33]
《狱中札记》中的领导权理论的当代性首先在于,它允许我们对现状以及通常理解这一现状的形式拉开一个理论的距离。一方面,葛兰西对于「政治域」的批判,将其作为历史性地生产出来的「资产阶级政治域」,为使左翼参与到当代政治哲学的规范性转向当中的诱惑提供了警告——这本身就是当代形而上学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于与日俱增的技术主义资产阶级哲学所导致的制度性危机的一个回应。特别是,它提供了一个论据,说明了为什么诉诸一种形而上学的——例如施米特的——政治域概念不能被认为是对持续存在的组织困难和左翼边缘化的解决方案,也不能被当作一种真正的「政治性」政治的基础。相反,就这一概念以理论形式再生产了支配着当下的官方政治的被动化的思辨结构而言,它正是问题的「本质性」部分。
与此同时,无论是在超越和远离了国家的「真正政治」中寻求,还是像马里奥·特隆蒂近来所提出的那样重返「(诸)劳动的世界」,尽管这些空间似乎可以逃脱政治域目前被构成的形式以及为这一政治域所批准的官方政治,葛兰西的进路也警告道,在这样的空间中寻找杠杆点的方法有着削弱力量的危险。[34]这些实践被辩证地整合在了整体国家中,已经臣服于资产阶级政治域的思辨逻辑所施加的过度决定,并被设定为这种逻辑加以沉思和在观念上进行协调的对象。求助于它们并不会找到一个未被污染的空间,使得我们可以从这个空间对现存的政治社会发动外部攻击;也不会发现一个潜能的领域,可以挖掘它用来在反对现今的寄生性权力、用制宪权 (constituent power) 反对现存事态的斗争中——像奈格里提出的那样——武装起来。相反,它会遭遇资产阶级政治域,或许还是其或许最为激烈和纯粹的形式,因为它声称「技术性的」组织具有非政治的地位——当然,这种组织在任何地方永远都是「自上而下」的。
在多种多样的实践以及组成了葛兰西所说的如今的「属下社会群体」的社会关系中已经存在着许多种组织形式,只有在对左翼理论与这些组织形式之间的有机关系加以更新的基础上,对于上面所说的那种实体化的具体否定才会发生:从「本能的」反抗到剩余价值的提取,到对作为社会需求之满足的商品形式的拒绝,再到对于「另一个世界」的方兴未艾的政治诉求。在当下的崩溃和居于属下的状态下,这些形式必然总是缺乏凝聚力而又收效甚微。然而,它们仍然是「由历史发展所给出的」形式;如果说它们仍然不是这样一种社会要素,在这种要素中,正如葛兰西对他那个时代的政党的描述那样,「集体意志在行动中得到了承认和肯定,它生成为具体的过程已经开始了」,它们依旧构成了能够产生出这样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具体的『幻想』」的唯一基础。[35]
在这样的形势下,理论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在于阐明「市民社会」中那些能够为未来的自我调节社会奠定基础的「原材料」(在「官方的」意义上是非政治域)。同样至关重要的是,正是为了将这些「原材料」从它们居于属下、被现存的作为思辨组织原则的政治域所询唤的状态下解放出来,理论还需要尝试在现存的「政治社会」的地形上,阐发一种新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实践,作为在大众阶层中建立起来的政治领导,这种实践能够挑战这一「政治社会」的思辨逻辑;在这些实践的形式中,理论的作用更多地为已经在进行中的方案揭示出「描述性的内在语法」,而不是提出一种规制性的实例,甚至是外在地设置的乌托邦计划。
当代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面临的主要挑战,并不在于如何尝试去阐明一种「替代方案」,一种左翼的政治域概念,以便最终让自己掌握政治域。这一挑战同样也并非主要在于批判现实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域以及得到其批准的政治哲学的概念性中所含有的规范性的、形而上学的自命不凡,甚至也不是批判它们如何持续性地侵扰这社会主义规划——这是绝对必要的。相反,今天的任务是尝试在哲学中实现「政治挂帅」:也就是说,将哲学当作社会关系的这样一种组织形式来加以实践,这种形式试图对具体的社会和政治关系和反抗实践进行恰当的理论「转译」,这样做本身就能够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政治域」。/
注释: [1] 本文的早期版本在「政治与思想」会议(扬·凡·艾克学院,马斯特里赫特,2008年9月27-28日)、「意识形态、真理与政治」研讨班(乌尔比诺大学,2008年11月13日)和现代欧洲哲学研究中心 (CRMEP) 的研究研讨会(米德尔塞克斯大学,2008年11月20日)上发表。我感谢对于这些活动的评论与批评意见,特别是Éric Alliez、Bruno Besana、Sara R. Farris、Fabio Frosini、Peter Hallward、Sylvain Lazarus、Peter Osborne、Ozren Pupovac、Frank Ruda、Alberto Toscano、Stefano Visentin以及《激进哲学》编辑部的集体。
[2] 目前的施米特复兴的许多主题都在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施米特转向中,特别是马里奥·特隆蒂在关于「政治域自主性」的辩论中得到了预示——这是政治理论的一个非常丰硕的时期,不幸的是,它在国际上的讨论中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3] 当然,对于施米特来说,政治域的特殊性体现在敌友区分的不可还原性。参见Carl Schmitt,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trans. George Schwab,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96。
[4] 这种先验「风格」并不是在现在时中,而是回溯性地进行的,它重构了记忆的可能性条件,以便在有条件的将来把它提出来:「激进的政治参与是存在的;它曾如何成为可能,又如何(再一次)可能成为可能?」就奈格里设定了现今激进政治的双重的内在-临近性 (immanence–imminence) ,需要的更多是揭示而非重建而言,他不被包括在这一进路中,尽管和「民主唯物主义者」奈格里或者他的对手巴迪欧和齐泽克所愿意承认的相比,从他的预设中产生的具体政治立场与这种进路可以说有着更多的共同点。
[5] Slavoj Žižek, 'Carl Schmitt in the Age of Post-Politics', in The Challenge of Carl Schmitt, ed. Chantal Mouffe, Verso, London, 1999, pp. 28–9.
[6] 博尔迪加对议会腐朽的最令人难忘的谴责是他在1926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上的介入。参见Protokoll. Erweiterte Exekutive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Moskau, 17. Febr. Bis Marz 1926, Verlag Carl Hoym Nachf, Hamburg, 1926, pp. 124 ff.
[7] Alain Badiou, 'De quel réel cette crpise est-elle le spectacle', Le Monde, 17 October 2008. 由Nina Power 和Alberto Toscano翻译为英文发表于www.cinestatic.com/infinitethought/2008/10/badiou-on-financial-crisis.asp。
[8] 关于倾向前一种进路的例子,参见Andreas Kalyvas, 'Hegemonic Sovereignty: Carl Schmitt, Antonio Gramsci and the Constituent Pri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vol. 5, no. 3, 2000, pp. 343–76。关于后一种的例子,参见Susan Buck-Morss, 'Sovereign Right and the Global Left', Rethinking Marxism, vol. 19, no. 4, 2007, pp. 432–51。这些综合或是纠偏所不得不否认的,不仅是最近的葛兰西文献学研究的发现(例如,参见Le parole di Gramsci: per un lessico dei 'Quaderni del carcere', ed. Fabio Frosini and Guido Liguori, Carocci, Rome, 2004;Fabio Frosini, Gramsci e la filosofia. Saggio sui 'Quaderni del carcere', Carocci, Rome, 2003),这些研究在决定性的方面纠正了先前被在政治上过度决定的解读对于葛兰西思想的扭曲,而葛兰西与施米特之间的这种有选择的亲缘性正是基于这些解读。它们还不得不抓住某些在修辞上表面有些相似的表述,才能忽略在葛兰西的哲学的彻底的此世性 (Diesseitigkeit),或存在的充实性与对任何虚空概念的否定,以及施米特思想的哲学基础——其最完善的形式是一种「法律虚无主义」 (juridical nihilism)——之间有着更为根本的矛盾(特别是在1923年的《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之后)。在哲学预设上,葛兰西和施米特位于现代哲学传统的两个完全对立的极端。
[9] 参见《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9卷,「论两个政权」,第131页——译注
[10] 参见Q 11, §46;Antonio Gramsci, Further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FSPN), ed. and trans. Derek Boothman,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1995, p. 306。关于列宁的原话,参见Collected Works 33, p. 430()。参考了葛兰西《狱中札记》的意大利文批判版:Antonio Gramsci, Quaderni del carcere, ed. Valentino Gerrantana, Einaudi, Rome, 1975。我采用了在葛兰西研究中被国际公认的引用标准,首先给出笔记本的编号 (Q) ,然后是个别笔记的编号。《狱中札记》的英文批判版由Joseph A. Buttigieg目前包括三卷,包含了笔记本1-8;这些卷数中包含的笔记同样可以按照笔记本和笔记编号进行定位。如果可能,我还会提供英文的葛兰西著作选集中的页码参考;例如这里的FSPN。
[11] 彼得·艾夫斯的著作 (Gramsci's Politics of Language: Engaging the Bakhtin Circle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Toronto, 2004) 的一大优点便在于,它强调,葛兰西的语言理论不能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可疑观念,仅仅被还原为所谓的「文化上的」关切,相反,它是葛兰西的整个计划的核心,特别是领导权的概念。
[12] Q 7, §35;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hereafter SPN), ed. and trans.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Smith,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pp. 356–7.
[13]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多次反对世界语,在他早期的报刊文章中也是如此,认为它为构成一种非等级性的翻译关系的真实困难给出了一个虚假的解决。
[14] Wolfgang Fritz Haug, 'Einleitung' to Antonio Gramsci, Die Gefänghishefte, vol. 6, trans. and ed. Wolfgang Fritz Haug and Klaus Bochman, Argument Verlag, Hamburg–Berlin, 1999, p. 1206. 葛兰西在入狱的早期翻译了《费尔巴哈论纲》。《论纲》成为了一块试金石,他在研究过程中不断返回到其中,以至于认为整部《狱中札记》是对于《论纲》——西方哲学传统中最短的一篇文本——的一篇扩展性的评注和阐发都绝非言过其实。
[15] Q 8, §22.
[16] Q 10I, §8; FSPN, p. 347.
[17] Q 10II, §2; FSPN, pp. 382–3.
[18] 参见Benedetto Croce, Logica come scienza del concetto puro, Laterza, Rome–Bari, 1967 [1908]。
[19] 「我们可以…说,每一种文化都有其思辨的或宗教的环节,这一环节与社会群体掌握完全领导权——它正是对这一领导权的表达——的时期是相一致的,或许它与这样的时刻恰恰也是一致的:真实的领导权崩溃了,但思想体系却像在罗马衰落的时代一样得到完善和提纯。批判将思辨解析为它的真实项即意识形态」(Q 8, §238;亦参见Q 11, §53;SPN, p. 370)。
[20]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ume 5, p. 89.(中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三卷,第80页——译者注)
[21] 按照葛兰西的著名定义,「国家是实践与理论活动的整个复合体,统治阶级不仅用它来辩护与维持自己的统治,而且还试图赢取受它所统治者的积极的同意 (consent) 」 (Q 15, §10; SPN, p. 244) 。为了防止反复的误读,有必要坚持这一点,那就是对于葛兰西来说,市民社会并不在国家之外(就国家是整体意义上国家而言),而是它的一个本质性的组成部分,政治社会能够通过这个被过度决定的形式将其合理性扩散到整个社会构型当中(比较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的表述,即「外部的国家」;G.W.F. Hegel,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 T.M. Kno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42, §183)。我在其他地方指出,葛兰西的整体国家概念中表面上存在的「二律背反」最好通过这种方法加以解决,即将其视为对于黑格尔国家理论的反原子主义预设的批判性阐发。参见Peter Thomas, The Gramscian Moment, Brill, Leiden, forthcoming。
[22] 阿尔都塞在阐述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时,为了反驳私人与公共之间的区别而提及了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的这个过度决定的维度。参见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trans. Ben Brewster, New Left Books, London, 1971, p. 144。
[23] 参见Q 25 §5;SPN, p. 52。亦参见Q 3, §90。
[24] 《狱中札记》中包含了不止一种,而是至少两种领导权概念(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它们代表了在葛兰西入狱前的政治活动中,特别是1922年共产国际四大以来已经得到体现的,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概念的阐发。到1929年第一本《狱中札记》写成时,葛兰西已经将其发展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一个「历史的、政治的原则」 (Q 1, §44) 或「历史研究的准则」 (Q 3, §90) 来应用于对资产阶级领导权的独特形式的研究;最后,在完成了这些历史研究后,葛兰西回到了他的出发点(特别是从1932年起),试图从理论上说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概念,特别是通过他的实践哲学概念来对其加以阐明。
[25] Q 7, §35; SPN, pp. 356–7.
[26] 值得强调的是,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的出发点是后革命形势,这尤其是因为人们尝尝声称,《狱中札记》中的领导权概念是源自列宁对于这个术语在前革命时期的运用,例如《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样的文本。然而,葛兰西在提及「现代最伟大的实践哲学理论家」这一重估,以及「用领导权学说来补充作为力量的国家 (State-as-force) 的理论」的观念时,明确地指出了他根本上参考的是列宁在后革命形势下,特别是在反对官僚化的斗争和对无产者和农民关系的处理中,重新制定领导权的概念与实践,将其作为无产阶级组织的一种形式。
[27] Q 13, §18; SPN, p. 161. 关于葛兰西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必然具有「经济的」和「道德-政治的」维度,亦参见Q 4, §38。
[28] Antonio Labriola, La concezione materialistica della storia, ed. Eugenio Garin, Laterza, Rome–Bari, 1965, p. 216. 关于葛兰西对拉布里奥拉在他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的孤独处境的评论,参见Q 16, §9;SPN, p.390。
[29] 关于葛兰西对先前关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一命题的表述——既在「唯物主义」哲学中又在「唯心主义」哲学中——所具有的局限做出的批判性评论,参见Q 11, §12; SPN, p. 334以及 Q 11, §54; SPN, p. 364。
[30] Q 15, §22.
[31] 参见EIIP13S。
[32] Q 10II, §12; SPN, pp. 365–6.
[33] Q 8, §21; Q 13, §1; SPN, pp. 125–33. Q 11, §12; SPN, p. 335.
[34] Mario Tronti, La politica al lavoro', Il Manifesto, 30 September 2008. 由Alberto Toscano翻译为英文,发表于http://conjunctural.blogspot.com/2008/10/old-guard-on-new-crisis-pt-2–mario.html。特隆蒂立即认定,应当认为这种复兴的「工人主义」姿态会对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一种大众的左翼」发挥作用,这股力量「在关乎选举之前首先是社会的」,但他并没有具体说明,这个「大众的工人政党」将如何与目前被构成的政治代表形式,或者与政治对这个先于选举的社会「基础」的过度决定相联系起来。
[35] Q 8, §21.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Philosophia 哲学社
推荐阅读:
版权声明:“备战深国交网”除发布相关深国交原创文章内容外,致力于分享国际生优秀学习干货文章。如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原谅,并联系微信547840900(备战深国交)进行处理。另外,备考深国交,了解深国交及计划参与深国交项目合作均可添加QQ/微信:547840900(加好友时请标明身份否则极有可能加不上),转载请保留出处和链接!
非常欢迎品牌的推广以及战略合作,请将您的合作方案发邮件至v@scieok.cn本文链接:http://team.scieok.cn/post/3693.html
-
- 左派的忧郁:马克思主义、历史和记忆 / 翻译
- 战争的逻辑:战略思维的高明之处,并不是赢在当下
- 什么是哲学 What is Philosophy: Subject Overview & Introduction
- 寒假社科营地:社会性别、从社会学角度理解疾病、国际关系入门
葛兰西与政治域:作为「形而上学事件」的国家到「哲学事实」的领导权
18932 人参与 2022年11月27日 15:36 分类 : 深国交哲学社 评论
search zhannei
深国交2024年英美本科录取小计
-

未标注”原创“的文章均转载自于网络上公开信息,原创不易,转载请标明出处
深国交备考 |
如何备考深国交 |
深国交考试 |
深国交培训机构 |
备战深国交 |
联系方式
Copyright www.ScieOk.cn Some Rights Reserved.网站备案号:京ICP备19023092号-1商务合作
友情链接:X-Rights.org |中国校园反性骚扰组织 | 留学百词斩 | 南非好望角芦荟胶 | 云南教师招聘考试网 | 备战韦尔斯利网| 备战Welles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