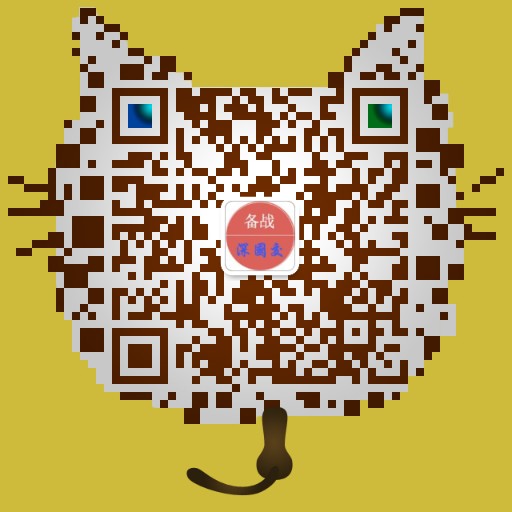当前位置:首页 » 深国交哲学社 » 正文
-
本文是美国政治理论家、女性主义哲学家Iris Marion Young《为了正义的责任》(Responsibility for Justice) 一书中的核心章节,其主旨在于发展一种能够回应结构性不正义 (structural injustice) 的责任构想,Young将此种构想称为责任的社会联系模型 (social connection model of responsibility)。这一模型在当前关于政治责任的思考中有不小的影响,除了Young着力讨论的住房市场与血汗工厂问题之外,在气候、环境、性别、动物保护等议题上也有回响。这一理论的最大价值或许在于启发我们设想一种不基于过错与罪咎的责任观念,从而扩充我们的责任语言和想象。
本文翻译初稿时借助了DeepL等翻译工具。文中重点由译者添加。

Responsibility for Justice 书封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本书的引导性问题:个人行动者和组织行动者应如何思考我们在结构性不正义当中的责任?这个问题蕴含着一些困惑和难题。一方面,正如我所论证的,存在不正义的这一判断本身就蕴含着某种责任。判断一种情况不正义,意味着我们认为它至少有一部分是人为造成的,也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纠正这种情况。另一方面,当不正义是结构性的,就没有明确的罪魁祸首可以归咎,因此也就没有明确应受纠正的行动者。
正如我在第 2 章中阐述的那样,结构性不正义是由成千上万或数以百万计的人生产和再生产的,而这些人通常是在制度规则范围内,按照大多数人认为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做法行事。比如说,一个在大多数住房市场中都很常见的现象是,有很大一批人缺少体面且可负担的住房。投资激励、开发商的想象力、专业水准和财务能力、有关住房偏好的文化假设以及地方规划政策等因素都会影响到这些市场的动态。在这些结构性过程中,有些人经常做出违法或不道德的事情。有些人可能会拒绝向黑人或看起来是穆斯林的人租房。也有些人会贿赂市政官员来确保对他们有利的区域划分。虽然这些非法或不道德的行为肯定是结构性后果的肇因之一,但从事这些行为的人并不是不正义的唯一实施者。有太多其他人牵扯其中。
法律和日常道德生活中分配责任的做法首先是要找到「谁干的」(who dunnit);要追究一个人对某一损害的责任,我们必须能够说是他或她造成了损害。要认定一个行动者应受责备或有过错,因果责任未必充分,但通常是必要的。这一一般化的原则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我们认为,当有些人的行为命令或促成了其他行动者直接造成损害,例如艾希曼安排火车的行为,那么这些人是应该受到指责的,有时甚至比直接造成损害的人更应该受到指责。这一类例外情况只是证明了这一规则:在道德和法律责任的标准框架内,有必要将一个人的行为与我们所要追究责任的损害线性地联系起来。
结构性不正义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法建立起这种联系。确定哪些人促成了结构性过程并不困难。然而,从总体上看,我们不可能确定某个特定个人、甚至某个特定的集体行动者 (如公司) 的行为,是如何直接对其他具体的个人造成损害的。例如,当住房消费者想要房前大草坪时,开发商迎合了消费者的这一愿望,可以说,满足这些愿望帮助抬高了一个地区的房价。但是,如果要说拥有大草坪的住宅小区的投资者或购房者的行为本身造成了一些低收入者难以找到价格不超出他们收入40%的住房,这是不正确的。许多其他行动、制度习惯和政策也造成了这些人所遭受的不正义。此外,特定人的行为并没有直接导致对其他人而言的不正义,而是通过对许多人的行为产生结构性限制和为一些人提供特权机会,间接地、集体地、累积地导致了不正义。
如果我们想说尽管如此,一些人仍对结构性不正义负有责任,那么我们就需要一种有别于标准构想的责任构想,标准构想侧重于个人行为及其与损害之间的独特关系。在本章中,我想提出这么一种替代性的构想,我称之为责任的社会联系模型。社会联系模型认为,所有那些通过自己的行动促成了那些导致不正义的结构性过程的人,都对不正义负有责任。这种责任并不像罪责或过错的归属那样主要是向回看的,而是主要向前看的。对结构性不正义负责意味着一个人有义务与其他负有同样责任的人一道,改变结构性过程,使其结果不再那么不正义。
我将把责任的社会联系模型与通常应用于法律和道德话语的构想进行对比,我将后者称为债责模型 (liability model)。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将结构性不正义的责任理论化的最佳策略是扩展和调整债责模型,但我认为这种方法存在问题。我将会论证,我们有充分的实践和理论理由,将与结构性不正义相关的责任当作一种特殊类型的责任,而非理解为罪责 (guilt)、责备 (blame)、过错 (fault) 或债责 (liability) 的责任的变种。

本文作者 Iris Marion Young (1949-2006)

债责模型的好处与限度
最常见的责任分配模型源于通过法律推理去确定损害的罪责或过错。在这一责任观念中,人们将责任分配给那些其行为可被证明与要求负责的事态 (circumstances) 有因果关系的特定行动者。这一行动者可以是一个集体实体,如公司。当它是集体实体时,出于分配责任的目的,可以将该实体视为一个单一的行动者。[1] 被认定与事态有因果关系的行为应被证明为自愿的,并且是在对情况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实施的。如果潜在的负责任者能够成功证明他们的行为并非出于自愿,或者他们有合乎情理的对情况缺乏了解的理由,那么他们的责任即使不能免除,通常也会被减轻。但当这些条件确实被满足时,将损害性的后果归咎于行动者便是恰当的。我将这一对责任的一般概念化称为债责模型。
对道德责任的构想,无论是在伦理学学者中还是在日常语言中,通常都预设了一个责任的债责模型。虽然人们通常会区分让人对某一事态承担道德责任和让人承担刑事或民事法律责任,但他们对责任的构想在形式上是相似的。说一个行动者有责任,意味着他应该因某一行为或其后果而受到责备。追究行动者道德责任的条件与追究法律责任的条件相似:我们必须能够证明行动者与有关损害之间有因果联系,而且行动者是在自愿,并对后果有充分认识的条件下做出行动。
刑法和侵权法有时也会以与这一理解有些不同的方式要求行动者对某一损害负起债责。不预设法律债责的道德责任的追究有时也会以下述的方式偏离这一概念。法律中有一个「应受处罚的过失 (culpable negligence)」的概念,在道德归责中有时也会用到类似的概念。它指的是,一个行动者对损害负有责任,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做什么。不过,这种归因之所以被称为应受处罚的过失,其目的是限制能恰当判定为应受谴责的不作为的范围。应受处罚的过失不作为参照的是对一个人应以特定方式行事的合理期望,这通常是因为他或她所担任的角色。例如,父母没有照看好孩子,可能就是一种应受处罚的过失。保安在有人闯入时睡觉,也是如此。
在侵权法中,严格债责 (strict liability) 的概念偏离了行动者应与损害有因果联系,方对损害负有债责的观念。在严格债责下,即使行动者不是造成损害的原因,也没有意图或无法控制损害的结果,法律仍要求行动者对损害负责,比如当一个人的财产造成另一个人的财产损失时。[2]
在我所称的债责模型当中,我将所有这些实践都囊括其中,即根据法律和道德判断分配责任,从而确定责任方,以达到制裁、惩罚或要求赔偿或补救的目的。尽管存在差异,但这些做法的共同取向是将特定行动者确定为责任人,而且其目的一般都是向回看的 (backward-looking)。
作为罪责、责备或债责的责任概念,对于法律制度和道德权利意识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这种道德权利意识尊重作为个体的行动者,并期望他们以尊重的方式对待他人。在应用这种责任模型时,应该有明确的证据规则,这些规则不仅涉及证明行动者与损害之间的因果联系,还涉及对行动者意图、动机和行为后果的评估。但我认为,债责模型并不适合分配与结构性不正义相关的责任。让我回到第二章桑迪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想说桑迪本人对生活在无家可归的边缘没有责任,但又想说她遭受了不正义,那么我们就是在说某些人要负责任。于是我们希望找到某些可以责备的人,或至少是某些应对问题作出补救的人。在住房行业的现实世界中,我们通常有理由找出个人和组织的过错,并让他们承担债责。房东频频任意拒绝将公寓出租给有孩子的单身母亲。非自住业主频频未能监督管理人员是否对楼房进行了适当的维护。在许多大都市地区,开发商和政府官员之间也往往充满了裙带关系和贪污腐败。[3]
不过,我在第2章中构造桑迪的故事时,有意将这些常见的过错搁置了起来,以凸显她的不幸遭遇主要是由个人、企业和政府机构的行为和政策的复杂组合造成的——这些行为和政策在大多数人看来是正常的、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必要且好的。
大量的行动者参与在产生这种结果的过程当中,其中许多人几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是如何造成这种结果的。房东们看到有利可图的报价,就会跃跃欲试,出售他们难以维护的房屋。城市培植想要翻新这些建筑的开发商,因为他们想要吸引商业投资,提升自己在债券投资者心目中的形象。年轻有为的专业人士搬回市中心,以方便工作和娱乐。低收入租房者竞争住房,导致住房需求模式发生变化,并以更高租金的形式反弹到所有租房者身上。每个行动者都在现有的法律和社会规范范围内为自己的利益而行动,他们的行动一道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一些人流离失所,难以找到体面又住得起的住处。我的意思是,没有人应该为这一结果受到责备,因为每个人的具体行动都无法在因果的层面上从结构性过程中分离出来,随后将结果的具体方面追溯回去。此外,这样的结果可能并非任何一个人的本意,许多人为其感到难过。在我看来,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应该承担责任,而是意味着他们应该在不同的意义上承担责任。

债责模型不适用于结构性不正义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是由许多人根据通常被接受的规则和惯例生产和再生产的,而这种结构性过程的性质决定了其潜在的有害后果无法直接追溯到该过程的任何特定促成者。我稍后将论证,在政治讨论中使用这种模型来概念化对结构性不正义的责任是不恰当的,因为它往往会引起人们的抵触防备之心,并进行 「甩锅」(blame switching)。受到第3章中论及的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认为政治责任有别于罪责的启发,我提出了一种责任的社会联系模型,专门用于思考与结构性不正义相关的责任。通过提出这一模型时,我并不是要取代或拒绝债责模型,而是在主张债责模型仅在一些而非全部语境下适用。
有些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不能扩展或改进债责模型来涵盖结构性不正义的问题呢?毕竟,债责模型下的集体责任理论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此外,法律理论和实践还发展出了复杂的关于共谋或协助和教唆的理论,这些理论将一些责任归于那些帮助、促成或支持他人做出应受责备之事的人。帮助他人的人、或以其他方式被我们判定为过错之共犯的人对过错负有共同责任,尽管其程度通常与直接肇事者或过错方不尽相同。探讨如何将共谋理论扩展到结构性不正义的问题上,难道不会比引入一个不同于我们在债责模型下熟悉的构想,能够得出一个更简单、更令人信服的责任论说吗?
预料到这一反对意见,让我稍作停顿,考虑一下克里斯托弗·库茨 (Christopher Kutz) 的共谋理论 [4] ,特别是他将这一理论扩展到类似于我用 「结构性不正义」一词提出的那些问题的努力。我认为库兹的努力并不令人满意,而了解其原因是很有启发性的。这是我所知的在这个方向上扩展债责模型的最佳努力。而如果这种模型下的最好的尝试尚且不能令人满意,那么我们就需要另一种模型。
库茨试图从理论上说明,在许多人参与的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中,共谋意味着什么,以及将人们视作共谋者的理由有哪些。他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轰炸德累斯顿作为一个详细讨论的案例。这是一个有数千人参与其中的任务;许多人在其中扮演不同角色,一些比另一些更重要,他们执行了不同的行动。虽然任务若要完成,许多人必须成功地驾驶飞机并向建筑物和其他目标投掷炸弹,但参与集体行动的一些人的行为可能与德累斯顿被烧毁没有因果联系,这也是事实。例如,他们的炸弹可能没有爆炸,或者可能落在了一个相对无害的地方。此外,对德累斯顿的轰炸是过度决定的。最终,落下的炸弹数量超过了将城市大部分地区炸成废墟所需的数量。因此,有些人的行为并不符合人们通常用来确认对某一过错的责任归属的,「如无行动,便不可能」条件 ("but for" condition)。这种条件指的是如果我没有如此行动,那么损害便不会发生,或者损害的程度不会那么严重。
库茨诉诸我们的直觉,认为每个参与轰炸德累斯顿的人都是这一过错的同谋。他的理论认为,使人们成为任何集体行动的共谋者的,是他们每个人都将集体行动的目标意图为自己行动的目的。每个人都有完成共同任务的参与意图。根据这一理论,那些发动机失灵、在到达德累斯顿之前便跳伞的飞行员与击中目标的飞行员一样是共谋者,因为每个人都参与在摧毁德累斯顿市的意图之中,并将这一目标作为自己行动的目的。
我认为这是对许多人参与并协作行动以产生确定结果的共谋行为的极佳论述。在其中一章,库兹将他的理论推广到这样一类案例当中,参与者集体造成了损害,但他们之间并没有协作,也没有意图造成损害的结果。他将这类案例称作「非结构性的集体损害 (unstructured collective harm)」。在我此处的讨论中,这个术语可能会引起混淆,因为我所说的「结构性不正义」的例子,正是库兹所说的「非结构性的集体损害」。在他看来,这些损害之所以是「非结构性的」,是因为它们不是一个协作达成的项目的结果。他使用的主要例子是全球气候变化,这是由向地球大气层排放化石燃料造成的。这是一种「非结构性」的集体损害,因为它是由许多人驾驶汽车、使用火力发电厂产生的电能等行为综合造成的。虽然其中许多人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参与了协作的集体行动,但没有一个人参与在一个旨在制造气候变化的项目当中。同样,在我看来,虽然许多人参与在产生某些不正义现象的结构过程当中,而且他们往往参与了某种协作行动,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所有人并没有参与在一个使某些人更易受到剥夺或支配的集体项目之中。从库茨共谋理论的角度来看,产生全球变暖或住得起的房屋稀缺的社会过程缺乏参与性意图,而此种意图是库茨看来认定人们对集体产生的结果负责的主要理由。
虽然如此,库兹认为,他可以通过对共谋模型作出调整,以涵盖这类集体造成的损害。他论证说,即使没有对集体项目的共同承诺,那些通过自己的行为造成损害的人与结果也有一种准参与关系 (quasi-participatory relationship)。他说,这种参与是准参与,因为并没有一个人们可以据以协调他们的行动的集体项目。相反,参与造成温室气体污染的个人 (或参与在造成住得起的体面房屋短缺的过程中的个人) 「都过着一种客观上明确且高度相互依存的生活方式。因为受害者指出的社会经济结构既不是自我产生的,也不是自我维持的。相反,它们产生于习惯和情感之间未经反思的合流,以及对于诸如私人交通价值一类事情的默契共识。这些都体现在无数的公共政策选择和私人行为中。事实上,只要成问题的社会经济结构是社会性的,它们就一定产生于个体行为者的动机,因为所有的社会活动都是个体活动。」[5]

Christopher Kutz, Complicity: Ethics and Law for a Collective Age
我同意库兹将产生污染的过程描述为结构性的,我也同意结构性的过程产生于个人的行为。这一事实的确可以作为将个人责任与结构性损害联系起来的基础。然而,如果库茨认为这种责任归属与他关于集体项目中共谋的理论是一致的,我认为他错了。我将他的共谋理论解读为属于责任的债责模型。那些与损害行为共谋的人与那些策划和指挥损害行为的人在同样意义上应受到谴责,尽管程度可能不同。他们做的事使他们参与在损害的实施当中,这是认定他们应受谴责的必要条件,但在我看来,却并非充分条件。他们之所以应受谴责,是因为他们理解他们的行为所促成的集体事业,并将这一集体目的内化为他们个人行为的目的。根据库兹自己的论述,在社会经济结构造成集体损害,但没有直接的协调行动的情况下,缺乏的正是这些条件。在没有产生结果的意图的条件下,参与其中的人不应像参与战争罪的人一样被判有罪。
我认为,从我的反对意见中能够得出的教训是,不应将与结构性不正义相关的责任视为共谋责任的一种削弱形式,而共谋责任本身则被看作个人刑事责任或侵权责任的削弱形式。当我们考虑与结构性不正义相关的责任问题时,量的差异变成了质的差异。我们应该追求的不是一种更弱形式的债责,而是一种全然不同的责任构想。
阿伦特将罪责与政治责任区分开来,就是为了凸显出了这一种类而非程度上的差异。只要我们参与在一个社会的持续运作当中,而在这个运作中发生了不正义,我们就应该承担责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罪或应受指责,或直接有债责向受损害者支付赔偿。这种债责意义上的责任应该留给那些可以具体指认为造成损害的人,他们通常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认为阿伦特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即模糊认定某人有罪或有过错的条件并不可取。把错误归咎于某个做了某件事情或处于独特地位可以防止其发生的人,往往是很重要的。这就意味着,在为结构性不正义分配责任时,我们应该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责任的概念。

社会联系模型
在日常语言中,我们对「责任」一词有几种用法。其中一种我已经讨论过了,其典范是债责模型:有责任就是因造成损害且没有正当的借口,而有罪或有过错。然而,我们也说人们因其社会角色或地位而负有某些责任,比如我们说教师负有特定的责任,或者我们呼吁我们作为公民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负责」并不意味着「有错」或在没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造成了损害;相反,它指的是行动者以道德上恰当的方式开展活动,并确保取得特定的成果。[6] 与债责的用法相比,我所提出的责任的社会联系模型更多地利用了「责任」一词的这第二种用法。然而,它与债责的用法一样,都要考虑产生不正义的结构性过程中过错的肇因。
责任的社会联系模型认为,个人对结构性不正义负有责任,因为他们的行为促成了产生不正义结果的过程。我们的责任来自于我们与他人共同处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合作与竞争过程系统之中,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寻求利益并致力于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这些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期望自己能得到正义的对待,而其他人也可以合法地对我们提出正义的主张。所有生活在这些结构中的人都必须承担责任,纠正他们所造成的不正义,尽管从法律意义上讲,没有人对损害负有具体债责。与不正义相关的责任不是来自于生活在共同的宪法之下,而是来自于参与在产生结构性不正义的各种制度过程当中。正如我将在第 5 章中讨论的,在当今世界,许多这样的结构性过程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使得分散全球各地的人们都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我通过将责任的社会联系模型与债责模型进行对比,来详述其特点。社会联系模型并不将受害者孤立出来。它将背景条件纳入评估范围。它分配责任的主要目的是向前看的。社会联系模型下的责任基本质上是共同承担的。因此,只有通过集体行动才能履行这一责任。

不孤立
正如阿伦特在区分罪责与责任时所强调的,确定罪责的目的在于关注特定行动者独个作出的行为 (done in their singularity)。同样,在侵权法中,目的是将债责分配给可孤立和可指认的特定行动者。一般来说,责任的债责模型试图将责任人标记并孤立出来,从而将他们与旁人区分开来,旁人由此不必承担责任。将有债责者与无债责者区分开来是刑法和侵权法中法律责任的一个重要方面。认定有罪、责备、认定过错或严格追究债责等社会实践的目的,都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行动者身上,以便对他们且仅对他们进行制裁或要求赔偿。对于道德规则和法律责任体系来说,重要的是所有行动者都知道他们可能会面临指控或被要求作为个体行动者承担责任。大多数关于集体责任的论述也旨在以这种方式孤立出肇事者,因为它们认为组织或集体和单个的人一样,都能为他们造成的损害受到责备。
另一方面,当成千上万或数以百万计的人参与到产生不正义的制度和实践中并造成损害时,这种孤立的责任概念是不充分的。在存在结构性不正义的情况下,认定某些人因实施了特定的过错行为而有罪,并不能免除其他其行动也促成了后果的人的责任,尽管后者或许要以不同的形式承担责任。假设一位房东拒绝将公寓租给珊迪,因为他担心这位单身母亲会有男朋友来过夜或无力支付房租。这种歧视是违法的,应该受到惩罚;这种偏见态度肯定会助长限制提供体面的住得起的房屋的过程,尤其是对单身母亲而言。然而,让人面临无家可归风险的结构性不正义并不能直接追溯到歧视者身上;这些行为与其他行为者的数百种其他行为一样,都助长了结构性不正义的产生。在存在结构性不正义的情况下,认定某些人实施了特定的过错行为,并不能免除其他其行为促成了这种后果的人的责任。此外,原则上,即使某些参与行动者没有做出任何现有的刑事、法律或道德的责备或认定过错的实践会认定为错误的行为,结构性不正义也可能持续存在。那些通过自己的行动参与制造和再生产结构性不正义的人通常是在管好自己的事,同时是在公认的规范和规则范围内行事。他们对不正义的结果负有责任,他们可能对此感到难过,但并没有具体的过错。因此,认定第三方负有责任,无论是从他们造成了可诉损害的意义上说,还是从他们在公认的制度规则范围内采取行动促成了不正义结果的意义上说,都不能免除他们 (我们) 的责任。

 判断背景条件
判断背景条件在责任的债责概念中,不论是要寻找肇事者的过错行为,还是要分配赔偿债责的损害,一般都被视为对一个可接受基线的具体偏离。我们假定有一套正常的背景条件,即使它们不是理想的,也是我们认为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犯罪或可诉损害是对这一背景结构的在道德上的偏离,通常也是法律上不可接受的偏离。[7] 我们通常将造成损害的过程视为一个单独的、有界限的事件,它打破了正在进行的正常状态。惩罚、补救或赔偿的目的是在基线情况的基准之上,恢复正常状态,或是「恢复完整」(make whole)。
另一方面,一种基于对行动者与结构性不正义之间经由中介联系之理解的责任模型,所做的不仅仅是对偏离正常和可接受的损害进行评估;它还经常对责备或过错之认定所假定的正常背景条件提出质疑。当我们判断存在结构性不正义时,我们恰恰是在说,至少某些正常的、被接受的行动背景条件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地助长了结构性不正义的产生和再生产,这正是因为我们遵循了我们所处的共同体和制度所接受和期望的规则和惯例。通常,我们以一种习惯性的方式执行这些惯例和实践,而没有明确地反思和考虑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更广泛的影响,我们的意识和意图首先想到的总是我们想要实现的直接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需要与之互动的特定人群。
如果我们的这种行为助长了产生结构性不正义的过程,我们就应对这种不正义负责。但是,通常情况下,我们不应在道德或法律上被判定为应受责备或有过错,原因有以下几点。我们通常不会把不正义的结果作为我们行动的目标,即使我们可以预见到众多行动聚合起来会产生那样的结果。此外,我们通常有理由认为,在这些公认的规则和惯例内行事是非常有德或有益的;而要理解在这些公认的规则和实践内行事的许多人是如何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从而产生许多人都认为是不正义的结果,则需要一个更广阔和更长期的反思角度。最后,我们有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采取其他行动的选择恰恰受到了我们所促成的结构的限制。
让我们回到住房的例子。在美国,家中有学龄儿童的父母在选择住房时,往往会主要考虑不同城市和社区的公立学校的声誉。许多家长认为,如果一个社区的学校过分拥挤或设备简陋,在标准化考试中成绩不佳,或在其他方面有不太理想的名声,那么他们选择在这样的社区居住是不合理的,对自己的孩子也是不公平的。许多家长意识到,当他们竞标学校理想的社区的房屋时,会导致这些社区的房价上涨,但他们表示,他们没有其他选择。这种动态可以说造成了不同社区和地区之间学校的不平等;更进一步,如果这种不平等导致一些儿童无法接受足够的公立学校教育,而另一些儿童却能接受优质学校教育,那么这种动态就应该被判断为是不正义的。住房消费者可能会助长这种不正义,如果他们选择了他们认为对孩子最好的学校,同时相信其他人也是这样做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明白,这一过程既造成了住房不正义,也造成了学校教育不正义,但他们也认为,由于自己无力独自改变这一过程,他们就必须顺应这一过程。

比起向回看,更多向前看
任何责任认定都具有多重时间性。因此,债责模型和社会联系模型都同时涉及过去和未来。不过,它们在时间上的侧重和优先顺序有所不同。例如,当法官、立法者或法律理论在考虑某些侵权损害时,他们有时会为未来的诉讼制定过错认定规则。一些刑事处罚和民事制裁就其目的是遏制它们所制裁的行为而言,也是面向未来的。然而,责备、追究罪责或追究过错的实践的主要目的是向回看的。我们试图为之追究行动者责任的损害或情况通常是一个已经到达终点的可孤立的行为或事件:抢劫已经发生,或者油轮已经将其内容物洒在了海滩上。如前所述,在这种模型下分配责任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应赔偿损害的具体有罪者或债责方。
而社会联系模型的重点的是向前看。我们试图为近期存在的、正在持续的、除非社会过程发生改变否则可能会持续存在的结构性社会不正义分配责任。由于特定个人或组织的行为与结构性后果之间的具体因果关系无法追溯,因此,试图只向所有促成后果的人寻求补偿,并按其参与的比例寻求补偿,将徒劳无功。通过结构产生的不正义并没有一个终点,而是持续存在的。关键并不在于为过去作出补偿,而在于所有促成了产生不正义后果的过程的行动者,努力改变这些过程。[8]
这一努力确实在一个方面上需要向回看。要理解结构性过程是如何产生和再生产不正义的,就需要一个对这些过程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从过去到现在是如何运作的解释。这种向回看的视角也有助于我们这些参与这些过程的人理解我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然而,这种向回看的解释的目的不是为了赞扬或责备,而是为了帮助我们所有人看清特定的行动、实践和政策与结构性后果之间的关系。

Janus的不同描绘

共同承担的责任
社会联系模型与债责模型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社会联系模型不会以默许免除他人责任的方式孤立出负有债责者。这一点的推论便是,所有那些通过自己的行动促成了产生不正义的结构性过程的人,都对这些损害负有共同责任。我的理解是,共同责任是我个人承担的责任,但不是我独自承担的责任。我在承担责任的同时,也意识到其他人与我一起承担责任;承认我的责任,也就是承认我作为其中一员的、共同产生出不正义的未成形集体的责任。我承担责任的根据在于,我参与了造成不正义后果的结构性过程。因此,我与他人共同承担着改变这些过程的责任,以减少和消除它们造成的不正义。我的责任就其本质而言是与他人共同承担的,因为这些损害是由我们许多人在公认的制度和实践中共同行动造成的,也因为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指认出我们自己的行为的什么内容造成了特定个人所遭受的不正义的哪些方面。
在思考共同责任时,我借鉴了拉里·梅的理论。[9] 梅认为,共同责任的概念有别于集体责任的概念,前者是一种分散的责任,而后者则不是。一个由人组成的集体,如一个公司,可以说要为某一事态负责,与此同时任何组成这个公司的个人可能都不在一个明确的意义上对该事态负责。另一方面,共同责任是指个人对群体所产生的后果或有害后果的风险负责。每个人都对后果部分地负有个人责任,因为后果并非他或她独力造成的;然而,每个人在造成结果中所起的具体作用是无法分离和指认的,因此,责任本质上是共同的。
梅的论述从概念上提出了共同责任的一般概念,这一概念可能有几种具体的形式。我在这里描述的与结构性不正义相关的共同责任就是其中的一种形式。尽管梅提示了这种共同责任,但梅理论的核心所念及的并非结构性不正义。他的主要例子涉及在社会群体背景下由可指认的的个人所造成的有明确时间范围的损害。他的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在一个人犯下仇恨犯罪一类过错的共同体中,共同体成员通常会持有与犯罪者相同的仇恨态度、或纵容这种仇恨、或不明确反对这种仇恨,从而助长了这种犯罪的发生。他的创新之处在于他提出,对于某些损害,不仅犯罪者在有罪的意义上要承担责任,而且周围共同体的其他人也要承担不同意义上的责任,因为他们与犯罪者有着共同的态度和倾向。
与结构性不正义有关的共同责任在几个重要方面与梅的概念不同。首先,总体而言,梅试图为之分配责任的过错更多适用债责模型。他将这些不法行为表述为偏离基线并已经到达终点的过错。
其次,正如我在第 3 章中分析的阿伦特的论述一样,梅所关注的不法行为有可指认的犯罪者,他们是有罪的;共同责任的理念适用于那些没有犯下过错,但其态度与犯罪者类似,且帮助营造了一种允许或鼓励伤害的氛围的人。另一方面,正如我所指出的,与结构性不正义有关的共同责任的一个特征在于,这种责任是要通过行动而非态度履行,其对象是常规和持续的过程。

唯有通过集体行动方能履行
社会联系模型有别于债责模型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向前看的责任只能通过与他人共同采取集体行动来履行。这一特点源于这一责任本质上的共同性。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数以千计甚至数以百万计的行动者通过我们的行动促成了产生不正义后果的过程。我们向前看的责任在于改变制度和过程,使其结果不再那么不正义。我们任何人都无法独自做到这一点。作为桑迪居住的大都市地区的一名房主,我无法独力改变房产价,或改变使公寓改建对开发商如此有吸引力的激励结构。当我们试图单独行动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客观上都受到了结构过程的规则、规范和物质效应的限制。只有来自社会结构中不同位置的许多行动者共同努力,对这些过程进行干预,试图产生其他结果,才能改变这些过程。
因此,我们可以再度援引阿伦特的观点,即这是一种独具政治性的责任,有别于私人的道德或司法责任。在这种模型之下,对结构性不正义承担责任意味着与他人一起组织集体行动来变革结构。最根本的是,我在这里所说的「政治」是指与他人的公共沟通往来,其目的是以最正义的方式组织我们的关系、协调我们的行动。那么,履行我对无家可归这一结构性不正义的责任可能涉及,我试图说服他人,这种对福祉的威胁是一桩不正义而非只是不幸,而这种不正义是我们共同参与其中的过程所造成的。我们将责成彼此努力改善我们的集体关系,并尝试改变原本不得不如此的实践。
这种意义上的政治通常包括政府行为,但并不能简化为政府行为。当代的正义理论和许多流行观点都倾向于认为,对不正义的补救是国家这一特定行动者的责任,而公民的责任则是向政府提出实现正义的诉求。社会行动者组织集体行动以纠正不正义的最佳或唯一途径是借助国家机构,这往往是正确的。[10] 然而,我们应该把政府的强制和官僚机构看作是那些共同承担责任的人协调行动的中介工具,而不是独立于我们之外的独特行动者。政府促进社会正义的政策通常需要共同体的积极支持才能奏效。
此外,那些对结构性不正义负有共同责任的人也可以通过公民社会的集体行动来实现社会变革,这些行动可以独立于国家政策和计划,也可以作为国家政策和计划的补充。例如,几十年来,在私人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下,城市土地信托运动 (urban land trust movement) 不断发展壮大,即使在住房市场本应「火热」的情况下,也成功地通过有限的股权安排,使一些住房的使用价格保持在可承受的范围内。[11]
与结构性不正义有关的责任由所有促成不正义产生过程的人共同承担这一观点的一个重要推论是,许多被认为是不正义受害者的人也要对不正义承担责任。在债责模型中,责备那些自称是不正义受害者的人通常是为了免除其他人对其困境的责任。然而,在社会联系模型中,那些可以被恰当地认为是结构性不正义受害者的人,也可以被要求承担他们与其他人共同的责任,即参与旨在改变这些结构的行动。事实上,在某些问题上,那些可能被认为在结构中处于较不利地位的人也许应该带头组织起来,提出对不正义的补救措施,因为可以说,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最严重的威胁。此外,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使不正义的受害者对问题的性质有独特的理解,并对其他处于更有权势和特权地位的人所提出的政策和行动可能产生的影响有独特的理解。在下一章中,我将详细阐述这一点。

政治中的怨恨与防卫心理
到目前为止,我在本章中已经论证了债责模型在概念上并不能很好地分配与结构性不正义相关的责任,我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责任构想,它具有向前看的特性,并且是共同承担的。基于社会联系的责任归根结底是政治责任,因为履行责任需要与他人一起确定能够改变结构、使其更少不正义的集体行动形式。
在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责任是政治的并非事情的结束,而是打开了另一个方向上的讨论。由消除不正义的共同责任所激发的政治,涉及一系列讨论和辩论,包括有什么其他可能行动方案、这些方案应如何实施、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在这种辩论中,就像在大多数政治辩论中一样,我们可以预见到冲突和分歧。在本章的最后,我将补充我关于政治话语中以责备或过错为导向的语言在概念和规范上的局限性的论点。这些局限更多的是修辞和实践层面的,而不是哲学上的局限。我认为,政治辩论中的指责语言往往会阻碍通向集体行动的讨论,因为它表达了一种怨恨的精神,生产出防卫心理,或者使人们更关注自己,而不是他们应该努力改变的社会关系。
威廉·康诺利 (William Connolly) 、温迪·布朗 (Wendy Brown) 和邦妮·霍尼格 (Bonnie Honig) 等政治理论家都表明,公众对社会问题和政治事件的反应往往是由一种怨恨的精神激发的。[12] 计划受挫或遭受无妄之灾的人们会将不快转而向外发泄,寻找可以指责的人,让这些人受苦来作为对自己的补偿。或者,有些可能认为自己有几分幸运的人,也会对他人被迫遭受的糟糕处境感到同情的愤怒,他们的反应也是寻找可以指责的行动者,而对这些人的惩罚至少可以宣泄他们的义愤。
上述这些作家在从事政治批评时都借用了弗里德里希·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对怨恨 (ressentiment) 作为西方道德的一种辩证产物 (a dialectic of Western morality) 的分析。怨恨的精神激发了尼采所谓的奴隶道德,这种道德具有这样一种内在生命的复杂性,这种内在生命可以感到伤害和痛苦,并且以转向外界作为应对伤害的手段。奴隶道德试图找到外部的、造成罪恶的强大行动者;奴隶道德的创造者试图通过罪责、惩罚和良知的规训对这些过错者施加一种反向的权力:
每个受难者都本能地寻找他的受难原因,确切些说…就是寻找一个造成了痛苦的有罪的行动者——简言之,就是随便找一个活物,使他能以任何借口直接对这个活物,或以其为模拟靶子,发泄他的情感,因为感情发泄是受难者的最大的取得解脱、即自我麻醉的尝试,是他为了减弱任何一种疼痛而不由自主地渴求的麻醉剂。[13]
尼采并没有简单地批评或拒绝现代道德的冲动,这些冲动作出责备的判断、试图归罪、并提出需要通过惩罚的反伤害来让人为过错行为付出代价。他说,这种道德造就了人类的内在性,造就了将事件在记忆中长久贮存的能力,并最终造就了具有责任感的主权主体的力量。然而,沉湎于怨恨精神却会导向虚无主义。归根结底,在他人血肉中为每一种伤害寻求等价物是不现实的,也是小气的:
恰恰是从最原始的个人法律权利那里,那些关于交换、契约、罪责、权利、义务、协议的萌芽意识首先将自身转化为最粗放、最基础的的社会筑物 (social complex)(在其与其他类似筑物的关系中),与此同时还形成了比较、测量和计算权力的习惯。[14]
负责任的自我确实需要深度、敏感和长久的记忆,但怨恨的精神最终会让那些指责者沉湎于过去:「他们撕裂最古老的伤口,让早已愈合的伤疤出血。」[15] 一个更博大的精神将会肯定,没法为每一损害都找到等价物,而向前走、走进一个改变了的未来,比起重新铭刻过往的关系,能够支撑起更大的力量。

尼采 要同意怨恨精神在政治上往往是有问题的,我们不必接受康诺利关于世俗化和全球化如何在当代政治中产生怨恨倾向的广泛论断,也不必接受布朗将所谓的「身份政治」作为这一问题的特定症结所在的观点。正如我在上文所说,我并不否认在许多法律和社会情境中,责备和认定过错的做法是恰当的。甚至可以说这种做法在某些政治情境中也是恰当的——例如,当一位公职人员在没有适当信息和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做出了灾难性的决定,或者当产生犯罪的行为是通过官僚的指挥系统产生的。我在此处全部想要论证的仅仅是,责备和认定过错的实践,以及这些实践背后经常存在的怨恨精神,在损害是结构性社会过程反复生产出的后果的政治问题上,通常无法取得成果。
在结构性不正义问题的语境中,指责的语言可能是不恰当的,也是无益的,因为它倾向于将人们划分为有权势的过错者和无辜者,不论后者是作为受害者还是旁观者。这往往过度简化了不正义的肇因,并使大多数人处于被动或相对无法帮助解决问题的境地。政治中的「指责」修辞通常试图找出造成问题的一个或多个特别强大的行动者,通常是一些政府官员。
有时这样做是恰当的。例如,由于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署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决定根据一项名为 「希望六号」(Hope VI) 的计划拆除全国各地的许多公共住房,如今美国有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或容易陷入无家可归的境地。他们承诺,因该计划而流离失所的人们将被重新安置在其他由政府补贴的经济适用房中,其中一些人已经得到了安置。尽管专家们可能对有多少人未能得到安置存在分歧,但很明显,很多人都没有找到政府资助的新住处,因为住房证书被削减了,已经或将要建造的公共补贴住房比最初承诺的要少。[16] 对于这些前公共住房居民所处的境况,希望六号的决策者以及那些决定不资助专门为他们建造和补贴经济适用房的人都难辞其咎。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行动及其后果,也会以一种牵涉到许多其他行动者的方式进入结构性过程,而这些行为者并不能合乎情理地因具体个人的境况而受责备。在公共住房项目开始被拆除后,许多公共官员和私人机构雇员的行为无疑都促成了可负担住房单元的缺乏和住房的市场价格。在这个更广泛、更复杂的系统中,住房开发和营销的过程未能提供人们负担得起的体面住房,对这些过程进行批评是恰当的,但如果我们寻求对几个有权势的行动者进行指责,我们就会让许多只是在完成工作的普通行动者免于责任。这样一来,公众指责的话语就会过度简化,无法发展出一个对造成不正义后果的行动和实践的公共理解。某些行动者的权力被过度抬高,而其他许多人的权力则被忽视了。
此外,在对社会问题的公共讨论当中,指责的修辞通常会产生出防卫心理和无益的甩锅。察觉到自己正因某些人遭受的错待而被责备的人通常会作出防御性的反应。在责任的债责模型下,对指责作出防卫性反应是一种自然而恰当的反应。指责的逻辑是,那些恰当地应受指责的人,即便作为一个群体,由于他们的特定行为以及这些行为或不作为与某些人为之寻求应受指责者的后果之间的独特关系,而对事件或情况承担独特的责任。我们在法律和道德上的指责和认定过错的实践允许被告作出回应,并提供证据 (如果他或她可以的话) 证明他或她的行为没有造成损害,或者解释他或她有免于指责的有效理由。
然而,在讨论的损害或和过错涉及大规模和长时段的社会结构过程的政治背景下,针对指控的防御心理通常是无益的,原因有几个。首先,它将辩论的焦点集中在过去,而不是现在可以改变什么。其次,指责和防御性反应会过度分化人们,在需要合作动力的地方制造不信任。此外,当有人指责自己应该为某件事或某一情况受到责备时,最常见的反应就是把指责的矛头转向别人。随后往往会出现循环往复的「指责游戏」,一个行动者接着另一个行动者受到指责,并通过将指责转嫁给另一个行动者来为自己辩护。在结构性不正义的语境中,这种甩锅尤其容易,因为其他人事实上确实通过他们的行动参与了产生不正义后果的过程。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所以很难将责任「钉」在某个个别的人身上。这种循环往复的讨论将会瘫痪以一种向前看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努力,因为我们一直在等待着孤立出应该作出补偿的各方。在下一章中,我将提出一个更有成效的方法,那就是接受我们共同承担责任的事实,并对变革任务进行责任分工。
让我提醒大家注意,在有关不正义的政治辩论中,指责修辞的最后一个问题。并不是每个受到指责的人都会做出防御性反应或试图将责任推给他人。有时人们会承认他们应受责备、或者有罪、或者有过错。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反应也无助于让人们团结起来解决问题的计划,因为人们会更加关注自己、自己过去的行为、自己灵魂的状态和自己的品行,而不是需要改变的结构。我们这些承认自己在制造不正义或未能阻止不正义方面有过错的人,会去忏悔,并检讨自己身上是否有冷酷或恶意的迹象。这种自我耽溺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这些注意力本可用于更客观地讨论社会结构是如何运作的,我们的行为是如何促成这些结构的,以及如何才能改变这些结构。
我在上文阐述的基于社会联系的责任构想提供了在政治当中使我们自己和他人负责任的方法,这种方法避免了诉诸责备、罪责或过错。如果我们用心倾听,我想我们甚至在当下都能听到政治语境中对这样一种责任构想的呼吁。在下一章中,我将重点讨论反血汗工厂运动中的一次这样的讨论。我所试图建言的是,如果我们能发展出一种独具政治性的责任修辞,并减少其中道德主义或司法语言的回响,那么关于社会和经济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的公共交流就会更加成功。在本章的最后,让我简要提及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对这种政治责任语言的一些提示,尤其是《友爱的政治学》(Politics of Friendship) 中的一些段落当中。

《友爱的政治学》书封 德里达并未停留于对怨恨精神的批判,而是更进一步,采纳了尼采关于对他人和历史的一种当下或未来取向的建言。在德里达的文本中,这种取向出现在「也许」(perhaps) 这一术语当中,德里达同时发掘了其名词和副词意涵:
要爱友爱,仅仅知道如何在哀悼当中承纳他人是不够的;还必须要爱未来。而没有比「也许」更适用于未来的范畴了。这么一种想法将友爱、未来以及「也许」联系在一起,从而向来者的到来展开——也就是说,一定是在一个其可能化必须超越出不可能的可能的体制当中。因为一个仅仅将会是可能的可能 (非不可能),一个确定无疑可能的可能,一个预先就能企及的可能,是一个贫瘠的可能,一个缺乏未来的可能,一个已经被打发到一旁的可能,或者这么说,一个其生命已确定下来的可能。[17]
德里达将尼采解读为在建立一种「逾越善恶」的责任概念,逾越出他说的我们从西方传统那里继承的等价交换和偿还债务的意义。这是一种对未来负责 (responsibility for the future) 的概念,是每个人单独承担、同时也与他人共同承担的责任:「我必须通过在我们面前、为我们作出回答 (answering for us and before us) 来在我面前、为我作出回答。我/我们必须为了未来的我、在未来的我面前,为现在的我作出回答,与此同时在当下将我呈递给你 (addressing myself to you),并邀请你加入这个你已然是却又尚未是其中一员的『我们』。」[18]
德里达对责任的讨论中带着很多列维纳斯的色彩。只要对他人说一句话,就宣告了一种对他者的责任。[19] 尽管对许多哲学家而言,自由主体是责任的起源,但在列维纳斯/德里达式的构想中,责任是自由的先导和根据:「这种责任将自由赋予我们,却又不将自由留给我们 (without leaving it with us),因为我们看到它来自他者。」[20]
我不打算对德里达的文本作全面的解读,甚至不打算作「忠实的」解读。在这里我只想简单说说这一「也许」的观念对于我本章的论证有什么启发,以及我所理解的,这一对政治中别种类型的友谊的呼吁。
在《友谊的政治学》中,正如在其他一些文本中一样,[21] 德里达批判性地回应了西方传统中许多哲学家对政治共同体的理解,这种理解援引了「兄弟情谊」(brotherhood) 的观念来描述一个政体的成员之间应该有的情感和义务的纽带。以对兄弟情谊的援引召唤出的政治友谊建立在同质性的基础之上,即对差异的否定——尤其是性别差异,但也暗含了所有个人和社会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会给在政治上寻求同侪感觉 (fellow-feeling) 的人们带来不对称的体验。德里达这本书的一个计划就是要探寻政治友谊的另一种含义。
我将把这种替代性的含义称为「团结」(solidarity)。作为一个术语和概念,团结不一定意味着相关者之间的同质性或对称性。有人用这个词来表示与他人的认同或一个群体的一致 (unity),但这种用法可以而且应该受到质疑。根据我的理解,团结是分散且彼此不同的行动者,当他们决定为了彼此站在一起后,彼此之间的一种关系。此外,团结与兄弟情谊不同,兄弟情谊诉诸的是从一个未被提及的母亲那里来的自然起源,它本来就在那里、可以指望得上,而团结则必须不断地塑造和重新塑造。团结是牢固的,但也是脆弱的。它看向未来,因为它必须持续被更新。
因此,将政治友谊理解为团结,可以从中解读出「也许」的观念。将自己视作和或近或远的旁人团结在一起的人会努力一道改善他们自己和/或他人的福祉。他们对历史采取积极的态度,这意味着他们不接受过去决定现在和未来的观点。他们不把现有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看作是既定的,而是把它们看作是一种可能性——也许事情可以得到改善。这种积极的立场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可以创造的未来,但它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让我们一起努力,尝试改变我们所理解的产生不正义的社会过程,也许我们会取得一些成功。为了正义而团结的人们决心改善社会关系,但他们也是如屡薄冰的 (tentative and humble)。在「也许」的激励和锤炼下,团结是对责任的呼唤:
如果此刻没有什么朋友,那就让我们努力行动,以便这种「至高的主人的友爱」(sovereign master friendship) 将来存在。这就是我对你的呼唤,回答我吧,这是我们的责任。友爱不是一件被给予的礼物,它属于期待、承诺和往来的经验。它的话语是祈祷的话语,它开创,却不记述,他不满足于现状,它移动到这样一个责任能打开一个未来的地方。[22]
我所援引的团结是许多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这些人认可并承担起与他们实施和支持的社会制度和实践相关的共同责任,以使这些制度和实践正义。这种团结是一种理想、一种承诺和一种参与。
德里达反思了责任的根本含义,它颇不同于一个可孤立的损害的肇因,也和等价交换和亏欠的隐喻有着距离。这些意义铭刻出了回应 (response) 的核心:去为某事/某物作出回答 (to answer for)、去回应、去在某人/某物面前作出回答 (to answer before)。
责任总是个人的,因为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作出回答。然而,为自己作出回答的命令假定了这种自我的中介结构,即我解释自己是因为我已经意识到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而他人要求我做出回应。因此,对他人作为回应的回答 (answering qua responding) 比为我自己作出回答更具有本源性。与他人的关系是先于自我的:「人首先回应他者:他者的问题、请求、祈祷、感叹、呼唤、招呼或手势、道别。」[23]
在为我作出的回答回应了他者之后,还有一种更为普遍的回答方式,即在某人/某物面前作出回答。德里达将此解释为往制度走了一步:「我们要在法庭、法律、陪审团面前作出回答,即在被授权合法代表他人的机构,即道德、司法、政治共同体的制度形式,面前作出回答。」[24] 这一司法-政治图景无疑是在某人/某物面前作出回答的一个实例。然而,在为了正义的责任的社会联系模型下,正如我所建议的,我们一般不会将人们带到正式的听证会或法庭上为自己答辩。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一些实践,就这些实践而言我们应该在一个政治体面前为自己的作为和不作为负责。明白自己在不正义和正义方面负有共同责任的人们会相互吁请,去在一个公众面前作出回答。政治进程旨在于形成这样一个公众,其中的成员提出问题和议题,并要求彼此采取行动解决这些问题和议题。/
注释 1. Peter French, Collective and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2. 例见:Tony Honore, "Responsibility and Luck: The
Moral Basis of Strict Liability," in Responsibility and Faul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4–40.
3. 托马斯·波格 (Thomas Pogge) 在一篇讨论责任转移策略的文章中讲述了一个房东通过改建公寓驱逐租户的故事来作为一个不公正行为的例子,我认为他想说这种行为在债责模型当中是值得指责的。参见:"Loopholes in Moralities," in Pogge, World Poverty and Human Rights: Cosmopolitan Responsibilities and Reform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 , 尤其是第77–80页。毫无疑问,一些房东的这种行为属于歧视或腐败一类,这超出了制度上可接受的公平游戏规则的范围。然而,他所举例子的意图与我在本文开头所举的例子不同,区别恰恰在于我们将房东看作在个人层面上应受责备是否是恰当的。我想说的是,有时责任并不是应受责备的过错 (culpability),而是与他人一起参与了产生不公正的结构性过程。
4. Christopher Kutz, Complicity: Ethics and Law for a Collective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5. Kutz, Complicity, 188.
6. Henry S. Richardson, “Institutionally Divided Moral Responsibility,” in Ellen Frankel Paul, Fred D. Miller, Jr., and Jeffrey Paul, eds., Responsib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18–249.
7. 参见:乔治·弗莱彻 (George Fletcher) 的论述,即刑事债责的分配必须区分行为与被假定为正常的背景条件之间的偏差,以及背景条件本身。Fletcher, Basic Concepts of Crimin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69–70.
8. 参见:Hans Jonas, 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 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90–120.
9. Larry May, Sharing Responsibi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10. 参见:Robert Goodin, "The State as a Moral Agent," in Goodin, Utilitarianism as a Public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8–46.
11. 参见:Thad Williamson, David Imbroscio, and Gar Alperovitz, Making a Place for Community: Local Democracy in a Global Era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12. 参见:William E. Connolly, Identity/Difference: Democratic Negotiations of Political Paradox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Wendy Brown, States of Injury: Power and Freedom in Late Modern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and Bonnie Honig,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Displacement of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13. Friedrich Nietzsche,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trans.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7), 127.
14. Nietzsche,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70.
15. Nietzsche,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127–128.
16. 参见:Larry Bennett, Janet L. Smith, and Patricia A. Wright, eds., Where Are Poor People to Live? Transforming Public Housing Communities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6) .
17. Jacques Derrida, Politics of Friendship, trans. George Collins (London: Verso Press, 1997), 29.
18. Derrida, Politics of Friendship, 37.
19. Emmanuel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 trans. Alphonso Lingis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69).
20. Derrida, Politics of Friendship, 231–232.
21. 例见:Jacques Derrida, Of Hospitality: Anne Dufourmantelle Invites Jacques Derrida to Respond, trans. Rachel Bowlb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2. Derrida, Politics of Friendship, 236.
23. Derrida, Politics of Friendship, 251.
24. Derrida, Politics of Friendship, 252.
文章来源于稷下大饭店
推荐阅读:
版权声明:“备战深国交网”除发布相关深国交原创文章内容外,致力于分享国际生优秀学习干货文章。如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原谅,并联系微信547840900(备战深国交)进行处理。另外,备考深国交,了解深国交及计划参与深国交项目合作均可添加QQ/微信:547840900(加好友时请标明身份否则极有可能加不上),转载请保留出处和链接!
非常欢迎品牌的推广以及战略合作,请将您的合作方案发邮件至v@scieok.cn本文链接:http://team.scieok.cn/post/4827.html
-
<< 上一篇 下一篇 >>
Iris Marion Young:个人是否能为结构性不正义负责?/ 翻译
32127 人参与 2024年12月18日 22:38 分类 : 深国交哲学社 评论
search zhannei
深国交2024年英美本科录取小计
-

未标注”原创“的文章均转载自于网络上公开信息,原创不易,转载请标明出处
深国交备考 |
如何备考深国交 |
深国交考试 |
深国交培训机构 |
备战深国交 |
联系方式
Copyright www.ScieOk.cn Some Rights Reserved.网站备案号:京ICP备19023092号-1商务合作
友情链接:X-Rights.org |中国校园反性骚扰组织 | 留学百词斩 | 南非好望角芦荟胶 | 云南教师招聘考试网 | 备战韦尔斯利网| 备战Wellesley